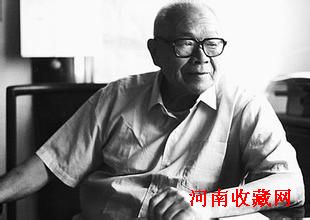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世襄先生是我国著名文物学家和重要的文物收藏家,他毕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退休前为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现虽年近九旬而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在长期的文物研究工作中独树一帜,自辟蹊径,开拓出很多当时尚无人注意的专门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为文物研究工作做出独特的、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王世襄先生研究范围广博,除对那些己近于文物中“显学”的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丰富的撰述外,尤致力于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具有一定工艺性质的文物乃至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种种器物,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琳琅美富的收藏和深入系统的研究,撰成多部专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
在王世襄先生的学术成就中,家具、髹漆、竹刻三门,尤称绝学。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王先生就对我国古代家具进行研究和收集标本,并在1957年发表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的专文,提出保护的原则和抢救的建议。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在做广泛的调查研究时也尽其所能进行抢救。经数十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也保存下一些为他进行研究所必需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优秀古代家具。随着收藏的日臻美富,他的研究也逐渐成熟和系统化。到浩劫过去,拨乱反正,藏品复归后,他即开始以全力进行研究和撰述,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了一系列论文和《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两部巨著。
明式家具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一株奇葩,在世界上也被公认为是一种典雅洗练、独具风格的重要家具流派,并对现代家具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近代编印明式家具图录始于外国人,通过他们,使明式家具之美,蜚声世界,其倡导传播之功,诚不可没。然而,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却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传统,并受当时的生活习俗、艺术风尚、审美观点所影响。那些著作主要是从形式美和它与现代某些艺术风格近似的角度去欣赏、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王世襄先生在其深厚的古代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学、民俗学基础上,全面地研究古代家具,在弥补了这些缺憾的同时,也就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
《明式家具珍赏》是介绍明至清前期中国古代家具的大型图录。书中精选了国内公私收藏精品一百六十余件,选例精当,文词深入浅出,既可使一般读者在赏心悦目的同时,能得到对明式家具全面、形象的知识,而书中很多卓越的见解和工艺技术要点,又足供做深入研究的津梁和设计制作的指南。纵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的两个意图。其一是不同风格兼收,既有淳朴洗练之品,也有装饰繁褥,不无纤丽,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特色之品。其二是在质料上高低并举,既有像宋荦紫檀大画案和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这类举世无双的“重器”,也有出自太湖水乡的质朴简洁的普通榉木民间家具。因此,本书不同于前此的著作之处是,它是一部不受个人爱好和目前风尚所左右的,力图历史地、全面地反映此时期家具全貌和发展进程的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同时又兼顾欣赏性的学术著作。
在前言和图版解说中,作者据其多年研究心得,提出了很多卓越的见解:如征引文献说明在明代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社会风气转变,出现了极力讲求家具陈设的潮流,而当时较松弛的海禁,又有利于珍贵木材大量进口,对硬木家具在此时期得以盛行并发展到高峰的具体原因作出了可信的分析;在发展源流方面,征引大量实例和图像,证实宋、明以来家具实际上存在着源于壸门床、须弥座的有束腰家具和源于建筑构架的无束腰家具两大类型,找出了家具结构与造型关系的规律;在制作工艺、装饰手法方面,对榫卯及线脚也做了深入的探讨,书中所收线脚多达七十二种,足觇一代风气;最后,还从室内装饰、陈设角度对明代家具布置特点进行介绍,并据他多年研究心得,提出明代家具布置疏朗,宜于多角度欣赏,而清代则偏于密集的差别,和布置家具应尽量使用同一类型,以便于求得和谐一致等意见。
《明式家具研究》是研究专著,全书二十五万言,图七百余幅,附有名辞术语简释一千条,根据实物,结合文献,对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地区、种类形式、结构、装饰、用材、年代鉴定诸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尤为难得的是,书中所收作者自藏的家具都由夫人袁荃猷女士对其结合方式和榫卯做精确测量,并绘成精美的图纸,图文对照,大大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本书后附《明式家具的“品”与“病”》一文,从欣赏角度把明式家具的优点概括为“十六品”,把缺憾总结为“八病”,精辟地指出其雅俗、文野之差异,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和赏析明式家具之美,以便正确运用本书中所提供的技术资料。
王先生研究家具除艺术层面外,重视工艺,是其最大特点。他所藏家具都经拆卸,一些小件家具收得后即拆成构件,捆绑在自行车后支架上载运回家。他也熟识很多老工匠,互相商酌工艺制作特点及优劣,所以他是从艺术和工艺技术两个方面对家具做全面研究。这两部著作前者侧重于艺术风格和审美,后者侧重于工艺和技术,二书相辅相成,建立起研究体系框架,对明式家具做了系统的研究,是建国以来首次出版的研究古代家具的权威性学术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学术上做出重要贡献,他也就当然地被公认为是这一领域的最权威专家和最重要的收藏家。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他也开始结合文献、实物和工艺技术对古代漆工艺和漆器艺术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成果最早体现在所撰《髹饰录解说》中。在1958年,此书只能署以作者的别号自费油印出版,分赠友朋,到1983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他参加了《故宫博物院藏雕漆》的编选并撰写了《中国古代漆器》和《中国美术全集·漆器》两部重要专着。他为后一书所写的《中国古代漆工艺》一文,广引考古出土物和传世精品,结合古代工艺专著和本人对当代漆工艺的调查所得,对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七千年间我国漆工艺的发展历史做了综合研究,实可视为一部中国漆工艺史的力作。他研究漆工艺也特重工艺,除反映在注释《髹饰录解说》中外,他也与老匠师共同探讨古代工艺特点和优长之处,并引古论今,对当代如何提高漆艺水平提出意见。他对中国古代髹漆技术进行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又开拓了一门新研究领域,使他成为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而他对当前漆工艺的关注也为日渐衰微不振的这项重要传统工艺技术取得新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建议。
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重要意义,被视为风雅的标志,晋人已有“何可一日无此君”的说法。除形诸诗文绘画外,竹制艺术品也成为古代工艺品的重要内容。竹制器物比之于金、玉、牙、角器,除雅致外,材质价廉易得,加工较易,也更具普及性,既可陈设于豪贵厅堂,也可成为文人寒士的案头雅玩,是古代传统工艺品中雅俗共赏的重要品类。王世襄先生的舅父金西厓先生精研竹艺,撰有《刻竹小言》,包括简史、备材、工具、作法诸章,并附述例,以实物加以说明,是近代关于刻竹艺术的重要著作。王世襄先生在整理西厓先生遗著的同时,也广搜实物和文献,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撰成《竹刻艺术》《竹刻》《竹刻鉴赏》三部专著。三书均在卷首冠以金西厓先生《刻竹小言》,其后则自撰专章,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除阐发西厓先生的研究外,其《竹刻概述》、《论竹刻的分派》、《此君经眼录》诸章,比之前人都有创获。在《此君经眼录》中,他广引传世器物,附以精美图片,加以考证,并与文献记述对照,形成一部近于刻竹艺术史图录的专章。结合公私藏品,对明清以来名家朱小松、朱三松、张希黄、吴鲁珍等作品的考鉴、认证工作,是他在这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由于他的努力,刻竹艺术这项清末以来日渐衰落的传统艺术又逐渐得到重视,其发展脉络得以理清。尤值得提出的是他在理清刻竹史的同时,还大力提倡振兴新的刻竹艺术,并特别重视创新成果。在《竹刻》一书中,他专文介绍了几位有创新成就的年轻刻竹艺术家,并在《此君经眼录》中熔古今于一炉,在明清名家重要遗物之后,一视同仁地以精美图版介绍了若干当代名家的创新之作。这样,他就在被公认为研究竹刻的专家的同时,也承担起支持继承和发展刻竹艺术的任务。这表明王世襄先生在研究古代艺术的同时,也关心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做到了“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对于毕生沉浸于古代艺术中的文物学家来说,是极难能可贵的品质。
在书画史方面,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撰成《中国画论研究》专着,建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五十年代初访美时,他遍览各大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尤关注绘画,收集了大量名画图片。他也是最早向国内系统全面介绍在美的大量中国古代名画者,论文网罗详尽,鉴定准确,在五六十年代是了解美国所藏中国名画的最重要的参考,有很高的研究和资料价值。对于中国古代书画的两件“龙头”作品《陆机平复帖》和《展子虔游春图》,他也做过深入研究并撰有专文发表。故虽因在“三反运动”中蒙冤受曲,被故宫博物院辞退,没有机会再多接触实物,不得不转变重点研究方向,以后也无暇再投入更多的精力,但这些成就已足以说明他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学术贡献。王先生不能按他的初衷进行绘画史研究,对他个人、对这个专业领域都应是一个损失,但迫使他转向其他专业,并发奋作出开创性的成果,对这些专业的发展又是幸事,这大约也可算做“坏事变成好事”的辩证法吧,但转化的条件则是他的执著和艰苦努力。
王世襄先生青年时曾参加过一些民俗性很强的活动,故有时被戏称为“玩家”,但和别的“玩家”不同,他在游戏之余,还注意搜集有关资料。晚年在此基础上广搜史料和实物,撰成专着,为这些时异境迁、日渐泯灭的民俗活动留下历史痕迹。他把经历过的豢养鸽、猎鹰、獾狗、蟋蟀、蝈蝈等都广罗古今文献史料和实物,追本穷源,形成一部部专着,在民俗学上做出杰出贡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