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些天,去郑州大河茶都三友堂喝茶,朋友常提起陈振博老师、龙开胜老师。在朋友的帮组下,今晚为陈老师制作专题,当我看到陈老师一幅幅精品力作,我被深深得折服了,同时也为河南书法人才济济,感到自豪和骄傲.......

陈振博 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美术评论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人画派的杰出代表,现居北京。国画专注人物,亦善山水、花鸟。在笔墨的洗练和凝重之间,作品之人物可见其魂魄,用水用墨已臻化境。书法独出机杼,出规入矩,师古不泥,大气洒脱,淋漓痛快。多年来浸研国学,在诗、书、画、论各领域自由穿梭。每作议论,指点画坛,激扬文字,影响深远。业余旁涉戏剧,问道医术。将各家之长集于一身,熔旁门别学于一炉,使其书画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有“神出鬼没”之誉。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获奖,另有多幅作品被韩国美术馆、新加坡南洋画院、抗日战争纪念馆、井冈山革命斗争纪念馆、国内外单位和政要名人收藏。国家级美术刊物,区内外电视台,海内外报刊等作过专题报导,个人业绩经美协等文化部门推荐收入《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等十多种典籍中,出版专著有《陈振博文集选》、《画坛忧思录》、《书画江湖》、《陈振博诗书画作品选》、《陈振博书画集》;主编有《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作品集》(八卷)、《当代书法名家作品选》等。
现任京华水墨画院院长、中国慈善书画名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京华书画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书协会员、新加坡南洋画院高级顾问、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央电视台书画大赛评委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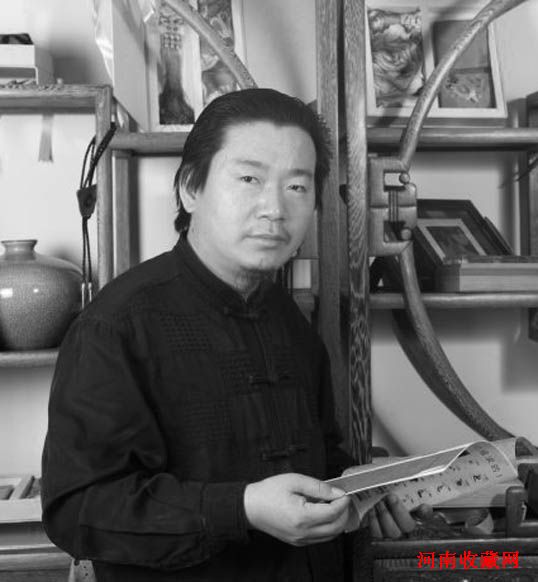
尝求古仁人之心
如何从根本上区分人的高低贵贱?我曾执着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标准,那就是“境界”。有文化、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有境界,有能力、有财富、有地位的人也不一定有高境界。境界不仅包括思想和修养,也是一种朴素的道德价值存在。前人对于境界的论述莫过于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所描述的三重境界被人奉为经典。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将最高境界解释为历经风雨的彩虹、无数坎坷后的坦途以及痛苦求索后的开悟。当然他这里主指事业和成就,而古人则把人生的最高境界做了更简单的定义,即“仁”。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涵盖了我们人生的全部准则。所以后世出现了以仁为旨的、形容和定义人的词语,如:“仁人君子”、“仁人志士”、“仁心仁术”、“杀身成仁”等等。做一个“仁人”,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士大夫的终极目标,是其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
“仁”,代表了古代文人的责任与情怀,是古代文人思想与追求的高度概括和凝炼,寄托了他们全部的价值渴望和道德理想。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为了成为“仁人”。宋代的范仲淹在其《岳阳楼记》中不仅表现了对于“古仁人之心”的向往,还列出了具体的实践准则和要求规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追寻“古仁人之心”的范仲淹和表现“仁人”思想的《岳阳楼记》都成为了后世的楷模。我对范仲淹和《岳阳楼记》的敬仰与喜爱,也大致是来源于此。少小离家的我后来得知故乡竟然与范仲淹有着极深的渊源,这更让我对“古仁人之心”的向往有了近距离的情感依托。
我虽然从事书画创作多年,但从来没有好好地总结过自己,不知道投向什么主义或者追随什么风格,只求能直抒胸臆而已。但心中“古仁人之心”的印痕以及那种文人化的气息却总是挥之不去。去年一个朋友给我举办了一个展览,在总结分析我的作品之后,冠以“古仁人之心”的称谓。这令我感到怵然,自觉惭愧,不能担当。它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激颤之余,不禁也思考:我画孤傲的李白、忧伤的杜甫,深沉的陆游与悲愤的屈原等,不正是我内心的向往、寄托与写照吗?不也是我所的求“古仁人之心”的体现吗?想到此处便也释然了。胸中存有大抱负,笔下才有高境界,夜深寂静,万籁无声,掩卷深思,时而喟叹,想守住一份孤独,又要面对热闹烦扰的市场,就须用“仁人之心”来化解这些迷茫与困惑。在自己的内心,就要驻守一个倔强的灵魂,去摒弃那卑屈的人格,远离那欲望的折磨,洗刷那无知的狂妄。“古仁人之心”就像一盏明灯,给我一个持续的光亮和指引,让我拥有一种具有深刻力量的精神现实,用于弥补自我与非自我、欲望与满足、欢乐与痛苦之间的裂痕。那仁人之思、那理想的境界在支撑着我的追求,那种强烈的渴望让人亢奋,那深远的思虑让人神游物外,让人进入忘我之境。它让我拿起画笔,去倾诉求索的孤独、内心的彷徨、思绪的飞翔和悟道的灵光。每在此刻,就好像有金色的佛光在笼罩着我的全身,我感到了无限的温暖和光明,那是一种不可明状的愉悦和幸福。这就是我喜欢的状态和能够进入的境界,也是我坚守的原因。
想起《齐白石山人南归序》开篇所讲:“入名利之市,辄能施其智巧以满志而充欲者,则其人必皆便捷之秀、识时达变之君子。”我认为这是能够教导书画家们如何在当世生存发展的一种高境界,既食人间烟火,也要做出自己,这是符合“古仁人之心”的,只可惜真正能够领悟的人不太多。如果说“仁”包含着人生大义和社会责任,在艺术创作中,它同样也包含着个性本体的表达和诉说。人本体有社会属性,人性的表达必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社会意义,所以“仁”是提倡和包容艺术家发挥个性的,于此我也找到了个性张扬的基础与归宿。对“古仁人之心”的追求,不容我分心和懈怠。时间的紧迫感和个人修为要求,让我需要对现实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且一直被督促着、要求必须沿着正确的方向艰难前行。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却不时地又伴着忘形的自信、难言的悲哀与深深的抑郁。一个艺术家生命的曲线必然是引吭高歌划破长空后复归于自然的沉寂。所以,矛盾是我的宿命,当然,这也是另一种境界。
今天,面对彷徨求索的结集,我用时常哀伤的情绪与倔强的意念来为它添上一丝寄托,谓之序。

